8/1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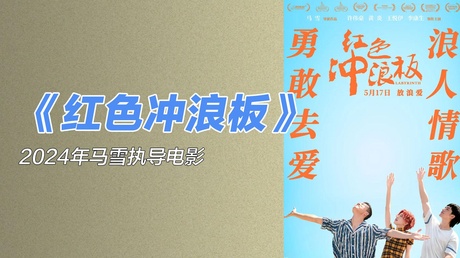 故事的开篇吊诡弥合了历史与当下两种真实性时空,谋划逃亡、警报戒严等历史幽魂纷至沓来,穿着特警队制服的纳粹军队挤满了街道、火车站和群租房.
故事的开篇吊诡弥合了历史与当下两种真实性时空,谋划逃亡、警报戒严等历史幽魂纷至沓来,穿着特警队制服的纳粹军队挤满了街道、火车站和群租房. 边境的含义不再是简单将二战屠犹和欧洲移民潮的两种时代创伤进行相互指涉,更是个体身份与记忆的错置,如何承担新身份过去的记忆和接受一份错认的爱,成为主角一种既达不到也离不开的状态. 主角频繁地造访马赛的墨西哥和美国领事馆,这里有来自不同背景的申请人,遛狗的中年妇女,穿着整齐的老人,错认为作家遗孀的哑巴母亲,陷入困境的人不断萍水相逢,在苦难的年代似乎救谁也不重要,最终主角询问得知开往美国乐土的船触到水雷遇难,历史与当下的精神阵痛未达到终点就已翻船. 导演将视点隐匿在客观叙事与旁白的暧昧交错中,就像男主证明作家身份逃离是非之地的那份遗稿,有太多相似的苦难无人阅读. (格里菲斯运用了平行蒙太奇手法,把时空相距甚远的不同活动剪辑在一起,让四个故事“巴比伦的沦陷”“基督的受难”“圣巴戴莱姆教堂的屠杀”“母与法”交替出现. 从一个世纪跳到另一个世纪,从一个事件跨越到另一个事件,情节的平行铺展造成了逐渐强烈的紧迫感,形成巨大的感情冲击和惊人的视觉效果. 一个摇着摇篮的母亲的隐喻画面反复出现,借此起到连贯影片主题的作用,象征在不同的时代,人性中的永恒的命运主题─党同伐异:党同伐异驱使善良而有同情心的人们把城市变成了暴力的场所,驱使妇女卖淫,逼迫母子分离,并且几乎驱使一个无辜的人走上了断头台. 格里菲斯对电影剪辑、叙事节奏、情节结构和移动摄影等技巧的大胆运用,宏大的群众场面等使得爱森斯坦和普多夫金等人在其基础上深入探索,最终建立蒙太奇理论,将电影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
边境的含义不再是简单将二战屠犹和欧洲移民潮的两种时代创伤进行相互指涉,更是个体身份与记忆的错置,如何承担新身份过去的记忆和接受一份错认的爱,成为主角一种既达不到也离不开的状态. 主角频繁地造访马赛的墨西哥和美国领事馆,这里有来自不同背景的申请人,遛狗的中年妇女,穿着整齐的老人,错认为作家遗孀的哑巴母亲,陷入困境的人不断萍水相逢,在苦难的年代似乎救谁也不重要,最终主角询问得知开往美国乐土的船触到水雷遇难,历史与当下的精神阵痛未达到终点就已翻船. 导演将视点隐匿在客观叙事与旁白的暧昧交错中,就像男主证明作家身份逃离是非之地的那份遗稿,有太多相似的苦难无人阅读. (格里菲斯运用了平行蒙太奇手法,把时空相距甚远的不同活动剪辑在一起,让四个故事“巴比伦的沦陷”“基督的受难”“圣巴戴莱姆教堂的屠杀”“母与法”交替出现. 从一个世纪跳到另一个世纪,从一个事件跨越到另一个事件,情节的平行铺展造成了逐渐强烈的紧迫感,形成巨大的感情冲击和惊人的视觉效果. 一个摇着摇篮的母亲的隐喻画面反复出现,借此起到连贯影片主题的作用,象征在不同的时代,人性中的永恒的命运主题─党同伐异:党同伐异驱使善良而有同情心的人们把城市变成了暴力的场所,驱使妇女卖淫,逼迫母子分离,并且几乎驱使一个无辜的人走上了断头台. 格里菲斯对电影剪辑、叙事节奏、情节结构和移动摄影等技巧的大胆运用,宏大的群众场面等使得爱森斯坦和普多夫金等人在其基础上深入探索,最终建立蒙太奇理论,将电影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